「厭女」、語言多義性
最近關於「厭女」的討論,我想部分起火點在對「厭女」有不同定義:
一方所採概念較偏女性主義關於「厭女」的分析;
他方則以字面上意義的「厭斥女性」出發,認為該人出於自身經歷才對他人言行有負面、扭曲評價,並非刻意針對女性群體,因此不算「厭女」。
雙方交流時,易將對方「從不同定義的理解」解讀為「貼標籤、護航」、產生敵意,落入相互攻擊的惡性循環。
→關於「厭女」意思的概略討論,可見:
字面上意思;女性主義的討論;歧異解讀下的可能改善方式,尋求更合適詞彙或描述行為 朱家安:「厭女」就是討厭女性,對嗎?其實並不是 -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
朱家安:「厭女」就是討厭女性,對嗎?其實並不是 -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朱家安:為什麼歧視和厭女不見得都是出於「惡意」? -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
朱家安:為什麼歧視和厭女不見得都是出於「惡意」? -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朱家安:「misogyny」是否不該翻譯成「厭女」? -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
朱家安:「misogyny」是否不該翻譯成「厭女」? -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
我對「厭女」究竟該採哪個意義稍微保留。(下收
最近關於「厭女」的討論,我想部分起火點在對「厭女」有不同定義:
一方所採概念較偏女性主義關於「厭女」的分析;
他方則以字面上意義的「厭斥女性」出發,認為該人出於自身經歷才對他人言行有負面、扭曲評價,並非刻意針對女性群體,因此不算「厭女」。
雙方交流時,易將對方「從不同定義的理解」解讀為「貼標籤、護航」、產生敵意,落入相互攻擊的惡性循環。
→關於「厭女」意思的概略討論,可見:
字面上意思;女性主義的討論;歧異解讀下的可能改善方式,尋求更合適詞彙或描述行為
 朱家安:「厭女」就是討厭女性,對嗎?其實並不是 -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
朱家安:「厭女」就是討厭女性,對嗎?其實並不是 -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朱家安:為什麼歧視和厭女不見得都是出於「惡意」? -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
朱家安:為什麼歧視和厭女不見得都是出於「惡意」? -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朱家安:「misogyny」是否不該翻譯成「厭女」? -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
朱家安:「misogyny」是否不該翻譯成「厭女」? - TN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我對「厭女」究竟該採哪個意義稍微保留。(下收
一方面,女性主義脈絡下的「厭女」,可見「一個群體為身上無以名之的雙重枷鎖命名,而得以促進討論、團結爭取權利」的歷史,雖字面意義可能產生誤解,但也不宜直接放棄過往歷史蘊含的複雜、多層次經驗;
另方面,出於望文生義而將「厭女」解為「仇恨女性」雖有其問題,但人類感受與經驗的多樣性而造就的語言多義性、語言除了溝通以外的功能,使得語言難以追求「唯一正確的意義」,也就難以認定將「厭女」解為「仇恨女性」純屬個人惡意。
另方面,出於望文生義而將「厭女」解為「仇恨女性」雖有其問題,但人類感受與經驗的多樣性而造就的語言多義性、語言除了溝通以外的功能,使得語言難以追求「唯一正確的意義」,也就難以認定將「厭女」解為「仇恨女性」純屬個人惡意。
我個人會按情境使用,若對方也理解女性主義,直接使用「厭女」概念較省時省力;若是跟其他群體溝通,需更加留意誤解可能,適時說明自身使用的定義出於何種脈絡,或在必要時直接描述行為。
產生矛盾時,先停下來觀察雙方對概念、言詞是否有歧異理解,避免過快從「誤讀彼此意思」的誤會升級至「相互敵意攻擊」的衝突。
產生矛盾時,先停下來觀察雙方對概念、言詞是否有歧異理解,避免過快從「誤讀彼此意思」的誤會升級至「相互敵意攻擊」的衝突。
→語言的「多義性」: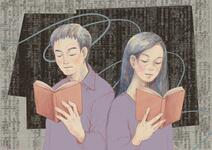 語言只是工具?別忘了感知複雜的自己!鄭毓瑜院士談漢字轉型 - 研之有物 │ 串聯您與中央研究院的橋梁//從古至今,隱藏在語言中的「多義性」打開了科學思潮之外,另一種觀看字句與意義之間複雜關係的可能性。//
語言只是工具?別忘了感知複雜的自己!鄭毓瑜院士談漢字轉型 - 研之有物 │ 串聯您與中央研究院的橋梁//從古至今,隱藏在語言中的「多義性」打開了科學思潮之外,另一種觀看字句與意義之間複雜關係的可能性。//
//上述案例看似在討論「文法」問題,其實真正該關注的是「修辭」,首先我們必須回到有血有肉的人本身來做思考,釐清人們使用語言可能有哪些目的?//
 The Concept of Language (Noam Chomsky)定義是對概念的提示;從經驗去理解概念的豐富性跟複雜性
The Concept of Language (Noam Chomsky)定義是對概念的提示;從經驗去理解概念的豐富性跟複雜性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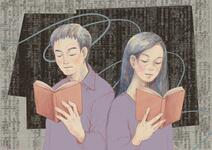 語言只是工具?別忘了感知複雜的自己!鄭毓瑜院士談漢字轉型 - 研之有物 │ 串聯您與中央研究院的橋梁//從古至今,隱藏在語言中的「多義性」打開了科學思潮之外,另一種觀看字句與意義之間複雜關係的可能性。//
語言只是工具?別忘了感知複雜的自己!鄭毓瑜院士談漢字轉型 - 研之有物 │ 串聯您與中央研究院的橋梁//從古至今,隱藏在語言中的「多義性」打開了科學思潮之外,另一種觀看字句與意義之間複雜關係的可能性。////上述案例看似在討論「文法」問題,其實真正該關注的是「修辭」,首先我們必須回到有血有肉的人本身來做思考,釐清人們使用語言可能有哪些目的?//
 The Concept of Language (Noam Chomsky)定義是對概念的提示;從經驗去理解概念的豐富性跟複雜性
The Concept of Language (Noam Chomsky)定義是對概念的提示;從經驗去理解概念的豐富性跟複雜性

-
「厭女」的雙重束縛:
「對女性從政者,這種『雙重束縛』(double bind),陷女性於困難的抉擇,類男性的女人才有領袖氣質,但太像男性缺乏女性特質的女性不受歡迎,而擁有女性特質又顯得柔弱無能。這種雙重束縛要求女性必須滿足兩者,只有其一者會受到懲罰。」// @wyc513 - #讀嘛讀嘛 《脆弱的力量》 //《脆弱的力量》是世界知名情感與同理心專家布芮尼.布朗...
@wyc513 - #讀嘛讀嘛 《脆弱的力量》 //《脆弱的力量》是世界知名情感與同理心專家布芮尼.布朗... @wyc513 - #讀嘛讀嘛 《這是愛女,也是厭女》 關於台灣厭女現象的專書,上篇剖析台灣各種厭女現象...
@wyc513 - #讀嘛讀嘛 《這是愛女,也是厭女》 關於台灣厭女現象的專書,上篇剖析台灣各種厭女現象...
「對女性從政者,這種『雙重束縛』(double bind),陷女性於困難的抉擇,類男性的女人才有領袖氣質,但太像男性缺乏女性特質的女性不受歡迎,而擁有女性特質又顯得柔弱無能。這種雙重束縛要求女性必須滿足兩者,只有其一者會受到懲罰。」//
若成為符合性主義sexism規範下的「好女人」,雖受社會「保護」,但也成為終身受他人宰制的客體(在家從父,出嫁從夫,夫死從子);
若成為反抗規範的「壞女人」,不是被排除在社群之外(社會性死亡),就是被安上罪名處死(實質死亡)。
不論遵循或反抗性主義規範,女性皆無從作為一個「有自主意識、能力,對自身生命有掌控權」的主體活著。
若成為反抗規範的「壞女人」,不是被排除在社群之外(社會性死亡),就是被安上罪名處死(實質死亡)。
不論遵循或反抗性主義規範,女性皆無從作為一個「有自主意識、能力,對自身生命有掌控權」的主體活著。
無論選擇何者皆受打壓的處境,易讓人產生「這個規範,乃至於運用獎懲方法來維持規範的機制,純粹是討厭、針對我吧」的感受。
或許是因為如此,先前的人才會將「運用獎懲來維護性主義sexism的機制」命名為「厭女」,來描述此種動輒得咎的困境。
或許是因為如此,先前的人才會將「運用獎懲來維護性主義sexism的機制」命名為「厭女」,來描述此種動輒得咎的困境。
-
「仇男」的意義;表達者與接收者的落差
我在求學階段曾被不只一位男同學評價為「仇男」。
當時總感到困惑,甚至不平。因從我的立場來看,我的言行是出於糾正刻板印象與歧視言論、反抗被客體化與矮人一截的對待等,出於防衛自己的正當行動,與「仇恨男性」無關。
但從同學視角來看,面對一個在互動中會不時皺眉,語氣直白地問說「你想幹嘛?」、「你這句話到底想表達什麼?」、「這個好笑在哪裡?」的人,大概不會認為這個人對自己是友善的。
在負面預設的本能、基本歸因偏誤下,不友善的行動易被解讀為帶有負面意圖,即「這個人出於對我的敵意、仇視才有了不友善的言行」。
我在求學階段曾被不只一位男同學評價為「仇男」。
當時總感到困惑,甚至不平。因從我的立場來看,我的言行是出於糾正刻板印象與歧視言論、反抗被客體化與矮人一截的對待等,出於防衛自己的正當行動,與「仇恨男性」無關。
但從同學視角來看,面對一個在互動中會不時皺眉,語氣直白地問說「你想幹嘛?」、「你這句話到底想表達什麼?」、「這個好笑在哪裡?」的人,大概不會認為這個人對自己是友善的。
在負面預設的本能、基本歸因偏誤下,不友善的行動易被解讀為帶有負面意圖,即「這個人出於對我的敵意、仇視才有了不友善的言行」。
回想當初互動,撇除歧視意味明顯的言論,我確實對男性的言行抱有偏高的警戒心、易往負面解讀。
「男生/女生都⋯⋯」的言論有著過於概括、刻板印象的問題,但也很常是節省溝通成本下的簡化敘述(預設對話雙方是共享同一語言脈絡的內團體)或人性普遍的認知扭曲。
揶揄、虧、刻板印象笑話,可被解讀為「不懷好意」之舉,也可能是某一群體慣性表達友好的方式。
當我以質問、指責因應,打破他們對同班同學應為友善內團體的預期,更易被評價為「反應過激、對男性抱有仇恨」。
雙方將彼此的「不友善」歸因爲「對方對自己有敵意」,未能意識到自身行爲對負面互動增添的柴火。
「男生/女生都⋯⋯」的言論有著過於概括、刻板印象的問題,但也很常是節省溝通成本下的簡化敘述(預設對話雙方是共享同一語言脈絡的內團體)或人性普遍的認知扭曲。
揶揄、虧、刻板印象笑話,可被解讀為「不懷好意」之舉,也可能是某一群體慣性表達友好的方式。
當我以質問、指責因應,打破他們對同班同學應為友善內團體的預期,更易被評價為「反應過激、對男性抱有仇恨」。
雙方將彼此的「不友善」歸因爲「對方對自己有敵意」,未能意識到自身行爲對負面互動增添的柴火。
價值觀衝突,可能意味著對自身安全的威脅,也可能只是分屬經驗極度不同的群體。在後者情形,敵意對待並非必要,只需拉出一個能讓雙方和平共處、滿足彼此需要的距離即可。
回頭看我跟男同學的相處,或許不需要在每次想法相左時都針鋒相對。擱置價值觀差異,把精力放在彼此的共通需求(課業、團體合作)上,更能有效建立信任、促進溝通效率。
回頭看我跟男同學的相處,或許不需要在每次想法相左時都針鋒相對。擱置價值觀差異,把精力放在彼此的共通需求(課業、團體合作)上,更能有效建立信任、促進溝通效率。
那種「非得糾正他們想法不可」的衝動,多半來自我有著「同學們應該是我的友善內團體」的期待,才會對他們的言論更感難以接受、企圖改變他們的想法。
從結果上來看,改變他們的行動是徹底失敗的,不僅沒有讓他們對女性的處境有更多同理,反而增加他們對我的不信任、防衛心。
為了增加我自身安全感的行動(讓他人想法跟我一致),卻導致雙方敵意更深的反效果。
從結果上來看,改變他們的行動是徹底失敗的,不僅沒有讓他們對女性的處境有更多同理,反而增加他們對我的不信任、防衛心。
為了增加我自身安全感的行動(讓他人想法跟我一致),卻導致雙方敵意更深的反效果。
「仇男」對男同學來說,或許想嘗試表達「他跟我互動時言行總被我放大、負面看待」的不受歡迎感受。
從字面上來看,「仇男」評價是針對我(接收者)而來,卻主要還是關於表達者的經驗、感受。
從字面上來看,「仇男」評價是針對我(接收者)而來,卻主要還是關於表達者的經驗、感受。
由這些經驗看來,可看出同一句話對表達者和接受者可能有完全相反的感受。
我從我的言行感受到捍衛自己的振奮、正義感,男同學卻從中感到被仇視、被禁言的受迫感;
男同學對我的「仇男」評價,或許是想尋求連結的友善提醒,卻讓我感受到被誤解、被惡待的敵視感。
當情緒、想法是以強烈的方式表達,就有更高機率被他人誤讀成勒索與控制,反使自身需求更難滿足;
將他人表達情緒、想法誤讀為對自身的勒索與控制,易陷入防衛反應,讓雙方皆無能自在行動、信任無從建立。
我從我的言行感受到捍衛自己的振奮、正義感,男同學卻從中感到被仇視、被禁言的受迫感;
男同學對我的「仇男」評價,或許是想尋求連結的友善提醒,卻讓我感受到被誤解、被惡待的敵視感。
當情緒、想法是以強烈的方式表達,就有更高機率被他人誤讀成勒索與控制,反使自身需求更難滿足;
將他人表達情緒、想法誤讀為對自身的勒索與控制,易陷入防衛反應,讓雙方皆無能自在行動、信任無從建立。
-
網路是個很混沌模糊的空間,很難像實體互動一樣拿捏關係距離。
一方面,網路是除去現實身份束縛的、很自由的空間,可以暢所欲言、跟更多人產生連結。
另方面,網路反而是更需要顧忌表達方式的公共空間。其自由性、打破空間性,讓我們即使是在自己版上發言,仍舊可能被預想以外的人看到、被討論。來留言者也可能不懷好意,甚至有高機會遇上因負向回應而獲得回饋感的酸民。
此種局勢容易脫離自身掌控的空間,表達更需注意會否讓不共享意義的他群體誤會。
網路的自由性對我來說,一方面給我發言需謹慎、留意雙方是否陷入雞同鴨講而無實際交集處境的提醒;
另方面也給我比實體互動更多的自由,在我認定對方沒打算跟我互動,或雙方價值觀差距過大,最適合「網路上的陌生人」距離時,直接不回應、取消追蹤或封鎖,而不需要花精力向他人解釋。
一方面,網路是除去現實身份束縛的、很自由的空間,可以暢所欲言、跟更多人產生連結。
另方面,網路反而是更需要顧忌表達方式的公共空間。其自由性、打破空間性,讓我們即使是在自己版上發言,仍舊可能被預想以外的人看到、被討論。來留言者也可能不懷好意,甚至有高機會遇上因負向回應而獲得回饋感的酸民。
此種局勢容易脫離自身掌控的空間,表達更需注意會否讓不共享意義的他群體誤會。
網路的自由性對我來說,一方面給我發言需謹慎、留意雙方是否陷入雞同鴨講而無實際交集處境的提醒;
另方面也給我比實體互動更多的自由,在我認定對方沒打算跟我互動,或雙方價值觀差距過大,最適合「網路上的陌生人」距離時,直接不回應、取消追蹤或封鎖,而不需要花精力向他人解釋。
-
機器狼📷毛拍修圖
說
密技!吃頓大餐心情變好術 